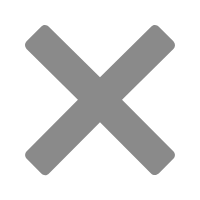-
世子嫌我是哭丧女,逼我做妾
本书由智阅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01
做哭丧女的第一天,假扮成神医的永安侯世子沈澈,对我一见钟情。
一年后,他三书六礼娶我为妻,我却在出嫁当日,被他的未婚妻拆了花轿,扒了嫁衣。
所有人骂我低贱晦气,配不上侯府世子。
沈澈觉得丢脸袖手旁观,任由我衣衫不整、受尽羞辱。
侯府扣押了我的嫁妆,大发慈悲允我做沈澈的通房。
沈澈逼我以心头血也为药引,为他的未婚妻做美容养颜丸。
沈澈拿着刀,看我如草芥:“乔儿,我知道他们在故意为难你,可只有你受点苦,才能永远留在我身边。”
我彻底死心,当空放出一支求救信号。
不久,女帝的凤凰骑兵将侯府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女帝最狠毒的鹰犬跪在我脚下,眉目阴鸷:“公主现在相信,外面都是豺狼了吧?”
1
“乔儿,母亲让你先去给婉吟道歉,嗑足九九八十一个响头,再回来取心头血。”
沈澈握紧我的手,眉眼疏冷:“别怕,我会陪你一起去,杨家绝不敢对你下手。”
我抽回手,看了眼屋外刀锋出鞘的护卫,冷笑道:“你知道我的价位,五两银子哭灵一场,杨小姐是你的未婚妻,得加钱。”
沈澈瞬间变脸:“你在咒婉吟死?”
他看我的眼神,像在看毒妇。
“我跪天跪地跪父母,最穷的时候为了吃饭去跪死人,可我凭什么跪她?”
“她是妻,你是妾,你本就该跪她!”
婚书上写:马乔儿与沈清池结为夫妻,一生一世恩爱不疑。
我不是妾!
想反驳,却突然被无形的力量扼住了咽喉。
他不是神医沈清池,他是永安侯府世子沈澈。
我也不是哭灵女马乔儿。
我是三公主凌天骄。
婚书,作不得数……
“乔儿,为了我,忍一忍。”
沈澈一挥手,门口的护卫瞬间冲进来,按住我的手脚,给我灌了一碗药。
软骨散。
我哭灵时被疯子袭击,沈澈一碗药灌下去,疯子筋骨酥软,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那时候,他抱着我心疼极了:“乔儿,我会永远保护你。谁敢碰你一根头发,我要他的命!”
我被沈澈丢在杨小姐的闺房外,额头嗑在花台上,粗粝的砖石拼命往我的皮肉里挤。
我动不了。
只能清晰地感受到,那块皮肉被磨穿、磨烂。
花圃的缝隙里,沈澈扶着杨婉吟,姿态亲密。
可花轿被拆、喜服被撕的当晚,沈澈信誓旦旦地告诉我,他不爱杨婉吟。
不该信的。
杨婉吟偎依在沈澈怀里,声音细弱:“我可以说服自己不介意那个哭丧女,你呢?你能不能问一问自己的心?”
杨婉吟素白的柔荑戳着沈澈的胸口,半是嗔怪,半是勾引:“你逃避的究竟是我,还是这门强行塞给你的婚事?你曾因我一句戏言,数九寒天折梅相送;也曾因外人说了我一句闲话,便暗中让那人半个月下不来床。我不信你对我无情。”
我心里堵得慌。
雪天折梅,盛夏采荷,晚秋题叶,早春鸢飞,还有那细致无声的绝对维护,都是我无法忘怀的美好。
可在遇见我之前,他早就为别人做过了。
沈澈呼吸一滞,许久才从低哑的嗓子里挤出一句肺腑之言。
“顺从婚约,等同于背叛我曾经发过的誓,你说呢?”
我霎时如遭雷击。
沈澈特意找了一个与侯门格格不入的哭丧女,仅仅是为了和爹娘赌气。
“那她呢?你是真的喜欢,还是一时新鲜?她虽低贱,貌却不俗,所以才有许多主家请她去哭丧。面上是孝子贤孙,暗地里不知对哭丧女存了多少龌龊心思,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没被得手过。”
沈澈眼眸一沉,推开杨婉吟,嗓音发冷:“你们让她来磕头,不就是想毁她的容貌?我已经毁了,你别再折辱她。”
血流到了眼睛里,刺地我浑身疼。
我磕到额头,是沈澈故意的……
2
沈澈用最好的药给我敷伤口,可皮肉都烂了,必然要留疤。
“以后把左边头发放下来一点,就看不到疤了。”
沈澈的声音很轻,像他以千盏莲灯邀我月下游湖,为我挽髻梳头时的暧昧呢喃。
我望着他愧疚的眼眸,最后给他一次机会:“跟我一起离开京城,去朔方投奔二公主。”
我的嫁妆里有一把御造的短刀,沈澈认出来以后,我谎称自己曾是二公主的宫女,恰逢女帝大赦天下,得二公主赐刀归家。
沈澈包扎的手一顿,眼神变冷:“大公主和二公主为了东宫之位势如水火,你要让侯府也陷入党争?马乔儿,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永安侯世子?你接近我是为了替二公主拉拢侯府?”
他松了手,白色的纱布每落下一层,就把我和沈澈之间摇摇欲坠的信任斩落一分。
最终留在我掌心的,只有一片惨烈的血色。
沈澈第一次对我露出警惕戒备的眼神。
仿佛我是陷他全家于不忠不义的恶人。
而我,彻底死心。
永安侯夫人派了嬷嬷来催促沈澈取血,说药快熬好了,必得配上新鲜的心头血,再用人参鹿茸粉和匀,才能做得古书上的《人血养容丸》。
我想要正式入侯府,成为沈澈的妾,还需讨好杨小姐。
“世子真要取我的血?”
以前,我亲昵地唤他“清池”,偶尔也喊过“沈郎”,沈澈头回听见我喊他“世子”,眼神发颤。
沈澈失望至极:“你果真是二公主的狗!”
我冷笑:“我若死,侯府必亡!世子可得好生掂量。”
“二公主会在意你的死活?你信不信,只要我答应效忠,哪怕死一百个你,二公主也不会多问!你在那些人眼里,只是一颗随时可以舍弃、牺牲的棋子!”
“你不也轻易牺牲我、舍弃我?”
沈澈哑然。
屋里安静地可怕。
我故意做出“认命”的表情,收殓了满身的锋芒和怨怼,绝望地看着他,凄然一笑:“既然我注定要死,我一定要死在二公主赐的短刀下,你愿意成全我吗,沈郎?”
短刀里藏了一支信号弹,不出半个时辰,就会有人来救我。
沈澈眼眶微湿,嗓音低哑而坚决:“我不会让你死!”
他转身要走,我急忙抓住他,近乎哀求:“不给我刀,我现在就死。”
嫁妆被侯府扣押了,我不知道藏在哪儿。
我身上药效还没过,沈澈无须担心我提刀伤人。
他沉默了半晌,推开了我。
我无力地跌坐在地上,手掌蹭破了皮。
沈澈看不见。
只是离开时吩咐护卫,不许任何人进来,取血一事,必须他亲自动手。
一个时辰后,沈澈回来了。
我的刀就挂在他的腰上。
他在我心脏处开一个口做伪装,再用鸽子血瞒天过海。
“乔儿,我不怪你刻意接近,但从今以后,不可以对我说谎。”
沈澈往我嘴里塞了一颗药丸,捏着我的下巴强迫我吞下去后才松了一口气。
“这是我自己研制的毒药。”
“放心,只要你留在我身边,按时服用解药,我会保你一生无忧。”
我抬起手,攀上了他的腰。
他不安的眼眸渐渐平静,露出浅淡的笑意。
我却按住了刀柄上的机关。
3
没力气,按不动。
软骨散的药效是两个时辰,我看了眼窗外的阳光,最晚天黑之前,我就能发出信号。
期间,我扮演者被主子辜负的奴婢,和被迫认命做妾的绝望怨妇。
沈澈一直陪在我身边,侯夫人遣奴婢来叫过几次,他都没去。
身体渐渐恢复力气,我带着刀一步步挪到窗边,看着血色晚霞。
突然,老嬷嬷慌张奔来:“世子,杨小姐服用‘养容丸’吐血了!”
问完细节,沈澈的目光落在了我的手指上。
手掌破了皮,红肿结着薄薄的血痂,沈澈粗暴地抓过闻了闻,瞬间怒上心头。
滚烫的茶水直接淋在了我的伤口上,我疼得冷汗淋漓。
“我教你药物相生相克,是怕你误食中毒,你偷偷拿我的香囊害人,有没有想过那是一条人命!”
“她想要我的命,我以牙还牙有何不可?”
啪!
沈澈第一次扇我巴掌,没有半点迟疑:“你的命还在,她却要被你害死了!”
老嬷嬷小心翼翼请示:“杨家问责,老奴该怎么回?”
沈澈冷冷道:“煎药的丫鬟放错了药材,打死了送去杨家。”
老嬷嬷很失望,她和侯夫人都希望我早点死。
沈澈捏着我的下巴,恨铁不成钢:“那丫鬟才14岁,她是替你死的。”
毒药发作了,我抓着他的衣袖,疼到眼晕:“送我去杨家……不关她的事……”
沈澈一根根掰开我的手指,嗓音冰凉:“心疼她?乔儿,若是没有我,你也不过和她一样,卑微低贱,随时可以被推出去顶罪。”
他把解药丢给护卫,吩咐半个时辰后再给我。
我疼得满地打滚,沈澈走得头也不回。
我揣着短刀爬出门,护卫一脚碾在我后心窝。胸前的伤口裂开,沁出温热的血。
药圃里种了草乌,可镇痛,有剧毒。
护卫虽瞧不起我,却也怕我死了,无法向沈澈交代,连忙来抠我嘴里的草乌根块。
我早就把汁液吐在了刀刃上。
两刀,护卫见血,毒性发作地比我生嚼还要快,不久便浑身抽搐晕了过去。
而我终于暂时止住了疼痛,用力按下机关。
咻!
一团猩红的焰火在紫云下炸开,像二姐姐讲过的故事里,恶魔的眼睛。
我爬到池塘边大口大口地喝水催吐。
眩晕感不再继续加深以后,才从护卫那儿拿到解药。
我跌跌撞撞爬起来,往后厨的方向去。
无论如何,我得保住煎药的丫鬟。
后厨,沈澈往丫鬟要穴扎了几根银针,要她假死。
老嬷嬷赞道:“世子仁厚,待杨家见了尸体消了气,老奴就把她远远地送走,绝不让任何人发觉。”
沈澈洗了手,嗓音冷淡:“乔儿太要强,必得背上人命,才懂得过刚易折的道理。”
老嬷嬷见沈澈还不打算出门,便委婉提醒杨家那边催得紧,希望沈澈尽快去看杨婉吟。
“不着急。”
“怎么不着急?杨小姐都吐两次血了,您不是为此特意罚那位多疼一个时辰吗?”
“些许香料只会让人呕吐,她根本没吐血,只是觉得委屈,希望我去哄。你把乔儿的惨状悄悄告诉她,她心里会好受些。我就不去了,乔儿那边我得亲自去守着,否则还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。”
沈澈一转身,便看见了我。
脸色瞬变。
4
沈澈看见了我满身的狼狈,也看见了刀刃上泛黑的血痕。
他习惯性先发制人:“你用草乌杀人了?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草菅人命?”
我走过去,用他的衣裳擦干净了刀,凉凉道:“世子可知,遇见你之前,冒犯我者,死!”
沈澈讥讽:“不过是仗着二公主的势,狐假虎威。二公主远在朔方,你只能借我的势,所以乔儿,不要以为杀了两个人就能走出去,我要留你,你便连后厨那道门槛都跨不过。”
沈澈话音刚落,门房仓皇来报:“世子,不好了,乌月国质子带着羽林军,把侯府给围了!”
侯夫人也跟着找到了后厨来,焦急万分:“你父亲一大早被叫进宫,到现在也没有回来,如今外面全是羽林军,只怕是那阴毒狠辣的质子拿了咱们家的错处,带了圣旨要抄家。你速去向杨家求救,杨尚书是新皇夫嫡亲的大伯,必定能救侯府!”
沈澈顾不上我,急忙往后门去。
不久又折了回来。
侯府早已围得水泄不通,谁都出不去。
“乔儿,你认得乌月国质子吧?”
“颇有交情。”
质子八岁入京,在宫里住了十年。
沈澈吩咐:“你去打听打听,不管是要钱还是要别的好处,只要能保住侯府,都可以商量。”
“可以,但我要侯夫人当众脱下华服。”
出嫁那日,杨婉吟便是在侯夫人的支持下,命人撕碎了我的嫁衣,众目睽睽之下骂我淫荡下贱。
还鼓动围观的百姓一起羞辱我。
沈澈霎时怒上心头,抬手便要打我,可我已恢复力气,敏捷的躲开了。
老嬷嬷小声解释我的来历,侯夫人得知我曾是宫女,深得二公主信任后压下怒火,决定以大局为重,施舍道:“你若能解侯府之危,我让你做澈儿的贵妾。”
我冷笑着:“哪怕是沈澈的正妻,我也不稀罕,我只想看你脱衣服。你可以不答应,但凭我和质子的旧交,侯府若有三分罪,我能添作七分。夫人也别幻想杀我灭口,我若死,二公主正好有理由端了侯府。谁让你们左右骑墙,害二公主分不清敌我呢?”
侯夫人满脸羞愤,仿佛遭受了奇耻大辱。
沈澈也怨我斤斤计较、不敬长辈。
门房急禀:质子拆了侯府的大门,强闯进来了。
侯夫人绝望地闭了闭眼,咬着牙颤抖解衣,却被沈澈按住了手。
他是孝子,不允许任何人羞辱他的母亲。
我被撕嫁衣的时候,他却不曾如此维护。
那时候,我便该看清的……
沈澈的眼里再没有半点爱意,更无一丝愧疚,反倒露着轻蔑:“你曾为了一碗饭,自甘下贱去做哭灵女,便以为别人也像你一样,毫无底线?不要用你狭隘的思想,去揣度高门贵族的气节,沈家宁死不屈!你的毒还没解,我死,你也得死!”
最后一句,是威胁。
门房又来回禀:质子带着全副公主仪仗进府了。
侯夫人霎时从恐惧中抽离,眼神变亮:“我知道了,侯爷被叫进宫,是为了三公主的婚事。
当年三公主拒绝与质子联姻,陛下气得罚她去道观苦修,可三公主毕竟深得圣宠,这两年陛下一直在臣子中寻找合适的人选。
那质子必是心怀怨恨、嫉妒我儿,才会拆了侯府大门。待我儿尚主,定要将今日之辱百倍讨回!”
侯夫人挺直了腰杆,眸光变狠:“来人,扒了这贱人的衣裳,送去给阖府奴仆赏玩!”
沈澈要拦,侯夫人却说:“大公主和二公主斗得乌烟瘴气,三公主最得圣心,说不得将来还有大造化,你身边决不能有碍眼的女人。陛下居紫宸而知天下事,你和哭丧女的荒唐瞒不过,唯有虐杀哭丧女,才能向三公主证明你的忠心!”
护卫一拥而上,要将我拖下去。
我大喊:“珂屠尔,别藏了,滚出来!”